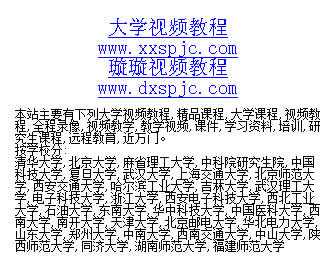听一个民族的歌声就能感受一个民族的气质。蒙古长调的苍凉悠远仿如游牧民族在草原戈壁上孤独的马蹄声,新疆歌舞的异域风姿使我们怀想神秘面纱后面那个高度发展的异质文明。歌舞是一个民族的代言人,她承载着流风余韵的积年铅华,惊艳于世人面前。聆听这些音乐之余,时常生出一许怅惘:我们的回族歌舞为何总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迟迟不愿前来相见?事情总是在柳暗花明处呈现转机,失望中潜藏着希望,哈晖的一曲《回族姑娘》应运而生,如金凤凰般飞临人们的耳畔,划亮了漆黑的沉寂。
“善良的动人的回族姑娘一生的心想只撒在一个人的心上……她是夜幕里最美丽的弯月亮……一生漂亮梦在了多少人的梦乡……”
那恬美婉转的歌声中分明有“花儿”的影子,那旋律熠熠生情,百听不厌,令人面红耳热的隐约透过那天籁般的歌喉看到一个多情且传统的靓丽女子。
作为一个自诞生之日起就在文化上具有高度水准的民族,他不缺乏米芾、郑和、李贽、白寿彝那样的一代风流。历史上曾从回族族源地之一的撒马尔罕传来中原一种舞蹈,它就是鼎鼎大名的“胡旋舞”。它在大唐风靡朝野。一身红袄绿袖的胡服打扮,在一小块毛毯上跳跃旋动的舞姿为盛事大唐涂抹上几笔世界主义的色彩。从回族先民的文化背景上看他们应该是能歌善舞富有艺术气息的一群。那为什么当代回族音乐的佳作如此千呼万唤、姗姗来迟?古人与今人的反差为什么会犹如天壤之别?这些问题隔着历史的重重迷雾,很难一眼望穿,姑且只能猜度了:原因大概有分布的不集中,政治经济自元以后的滑落,文化的遗忘乃至完全丧失。不过在西北人数稍为集中的地区还是在回族人中顽强的生存着“花儿”、“口弦”等艺术形式。

散心的花儿漫上的是青年男女初萌的情爱。
“哎哟哟——
西宁城我去过
有一个当当的磨
哎哟哟——
尕妹妹怀里我睡过
有一股扰人的火”
语言生动直白让最炽热的爱情诗句也自叹弗如。山间田埂中流出的民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最有生命活力的诗歌,《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各地民歌的集成。但“花儿”自古就被挤压在梁茆沟壑之间,被拒之在大雅门外。有人认为原因在教门中。其实真正的根子还在封建主义的底色不褪上。真挚的爱是顿亚(今世)里最美丽的情感,她缘何被罪?也好!就让“花儿”放歌山野,绽放在人们的心中,为回族音乐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源素养。
“花儿与少年”流传于青、 甘、 宁、新等地回族聚居区。回族擅长山歌,把这种山村的生活小调、男女间即兴对唱称“花儿”(河湟地区称“少年”)。1950年代后,一些回族群众在唱“花儿”时常作些简单的舞蹈动作,并吸收汉族民间舞蹈的折扇为道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自娱性的歌舞。据说,持折扇的表演最早由8名回族单身男子在民间社火中表演,称之为“八大光棍”。《花儿与少年》经专业舞蹈工作者改编后,成为融合回、汉文化的新型回族歌舞,深受欢迎。

羌民好歌舞,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节日聚会,或“红” “白”喜事,都离不开歌舞。婚有喜歌,丧有葬歌,喝酒有酒歌,耕地有牛歌。舞蹈也是无所不在,有歌就有舞,有舞亦有歌。不同的舞蹈配不同的音乐,边歌边舞,富有特色。羌族歌舞音乐曲式结构短小严谨,富有层次,句式对称,旋律明快活跃。舞蹈的形式多样,舞姿优美。最主要的有“沙朗” 舞、“克儿西格拉萨市”舞、“布兹拉”舞、“忍不拉·耸瓦”、“埃古·日格沙”等,所有的舞蹈形式独特,充满想像,极富艺术感染力。
羌族歌舞来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动。史料记载“羌王以牺牲祭奉天神”,《史记》说“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至今,四川北川、茂县、汶川、理县的羌族,仍用“祭山”的方式来延续传统的的祭祀。羌族舞以“沙朗”最为流行,相伴的舞曲也最多;以“克儿西格拉萨市”舞(“盔甲”舞)最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沙朗”羌语的意思是又跳又舞,也称为羌族“锅庄”。羌人住房都设有火塘,火塘上用油竹制成的“梭筒”悬挂鼎锅烹煮食物,火塘火种终年不灭。火塘是神圣的地方,在火塘边有许多禁忌。羌人平时在火塘边聚会、接客、用餐,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羌人把这种围着火塘跳舞叫做跳“锅庄”。舞蹈动作粗犷雄健,脚上动作多,手上动作较少,小腿特别灵活,上身微倾,扭腰送胯,勾脚踢腿,异常的奔放热烈。参舞者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圆圈,边歌边舞,愿舞者随时可以加入。歌曲大都是世代流传的古老羌歌,全用羌语演唱,由慢到快,舞蹈也跟着变化。开始轻柔舒缓,动作也温柔舒张,到后面歌声激烈奔放,响遏行云,动作也就大开大合,豪迈粗犷。数十人同声歌唱,手舞脚踏,如置身于千军万马。歌舞往往在高潮时嘎然而止,结束时众人齐声大吼,声势惊动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