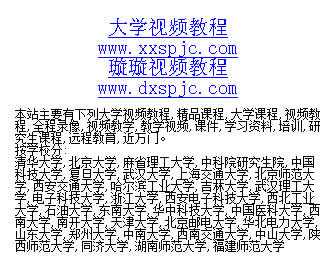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有一段小小的掌故。有人提出要出版马克思思格斯通信集。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夫人表示同意(这件事必须得到她的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我作为她的代理人参加该通信集的编辑工作。1910年11月10日,她从德拉伐尔写了一份委托书来,全权委托我作一些我认为必要的注释、说明和删节。
然而实际上,我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力。在出版者们之间,或者更确切些说,在出版者伯恩施坦(因为倍倍尔只是挂个名而已)和我之间,并未发生过任何重大的分歧。如果不是必要,那么我去乾涉他的工作,当然是没有理由、没有权利的,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否则就不符合委托者的初衷了。
但是,在编辑该通信集的很长一段时期中,由于以往多年研究而在我脑海里已经成型的卡尔•马克思的形象,变得更为鲜明突出了。因此,不由地想写一部传记来刻划这个形象。而且我知道,这个主意一定会使拉法格夫人非常高兴。我之所以获得她的信任和友情,绝不是因为我在她心目中是她父亲的最博学、最贤明的学生;而是因为,在她看来,我比别人更了解他的为人,因而也就能够在这方面描写得更为真实。她会不止一次地写信并且口头告诉我,说一些几已忘怀的关于她父母在世时的家庭往事,她在看到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特别是马克思遗著中的描述以后,又重新回忆起来了;还说她当年常听父母提到的一些人名,她因为我而跟具体事例联系起来了。
遗憾的是,当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出版时,这位品格高沿的妇女已经去世好久了。她在死前几小时还写了一封信来,对我致以亲切的问候。她禀承了父亲的豁达胸怀。她信托我出版马克思遗著中的许多珍贵材料,并且让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毫无乾涉之意。例如,虽然她明明从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已经知道,我曾经怎样经常在有关拉萨尔同她父亲的争论问题上坚决地替拉萨尔辩护,她还是将拉萨尔致马克思的信交给了我。对于这一点,我将永远感激她,至死不忘。
然则,这位妇女所具有的宽宏气度,在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卫道者身上却一点也找不到。当我着手执行自己的计划,即着手撰写马克思传的时候,他们两位就义愤填膺地大叫大嚷起来了。其理由是我在《Neue Zeit》[《新时代》]上竟没有完全迎合党内流行的说法,而就拉萨尔、巴枯宁两人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见。首先,考茨基斥责我“反对马克思”,特别是斥责我“辜负”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而因为我仍然坚持要把马克思传写下去,他竟然拨出《新时代》的如此宝贵篇幅中的整整六十页来刊载梁赞诺夫的抨击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企图确证我犯了最可耻的背叛马克思的罪行。他对我大加非难,其言词之歪曲捏造只能和其论点之荒诞无稽相媲美。由于某种感情(为了礼貌起见,我不愿说出这是一种什么感情)的驱使,就听任这些先生们肆意谩骂去吧,但是应该声明,我对于他们这种精神上的恐吓手段不会丝毫让步,并且在本书中叙述拉萨尔、巴枯宁两人和马克思的关系时始终以历史的真实为依据,而完全不理会党内流行的说明。当然,这时我仍然避免作任何争论,只是在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中对于考茨基和梁赞诺夫向我提出的主要责难加嘲讽,以便对做这方面工作的较年轻的人们有所助益,因为这些年轻人现在正应该养成习惯,对马克思主义教区的教士们的气势汹汹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如果马克思在实际上真像马克思主义教区的教士们所赞赏的那样,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年,那么我就不会醉心于写他的传记了。我的赞美,正和我的批评一样,——在一本好的传记中,这两者需要有同等分量——是针对着一位伟大人物而言的,这个人在讲到他自己时常常喜欢说: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把马克转的伟大形象不加修饰地重新塑造出来——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目的本身已经决定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历史向来同时既是艺术又是科学,传记尤其应当如此。现在我已记不起是哪一位古板的学者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种“不配的”言论,说在历史科学的领域内,美学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可是我应该坦白承认,——也可以说是我引以为愧的,——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也不像这些道貎岸然的思想家们那样使我深恶痛绝,他们只是为了打击伏尔泰老人,就宣称传记只能用枯燥无味的体裁来写3。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也被认为是糟糕的,因为他同意他所喜欢的古希腊人的观点,把克丽娥算作九个缪斯之一4。实际上,只有被缪斯看不起的人,才咒骂缪斯。
倘若我可以假定读者对本书所采用的体裁会予以赞同,那么我学得请求他在内容方面不要苛求。事先,我已经不得不考虑到,虽然这本书应该写得至少使文化程序较高的工人觉得通俗易懂,但也万万不可篇幅过大。可是现在的篇幅已经超过原计划一半了。我常常因此而不得不把一行紧缩为一个字,一页紧缩为一行,一印张紧缩为一页!在分析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时候,尤其为此感到苦恼。为了不使读者有任何误解起见,我把伟大作家传记中惯用的副标题“他的生活和著作”中的著作二字删掉了。
无疑的,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想成的。同样无疑的是,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在这方面,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有一致的看法。有一次拉萨尔说: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他们的看法有多么正确,在这们的时代,我们有着触目惊心的体会:那些用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时间来专心考察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逗点的一本正经的研究者们,本来到了可以而且必须像马克思那样行动的历史时机,却只是像风信标那样吱吱哑哑的绕轴自转。
不过,老实说,我并不自负比别人更能透彻地了解马克思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甚至为了要在我所叙述的狭小范围内,让读者对《资本论》第二、三卷有个充分清晰的概念,我还请了我的朋友卢森堡帮忙。因为她欣然接受我的请求,写了第十二章的第三节,读者们一定会像我一样的感激她。
我的这本书由于她的珍贵手笔而增色,我为此感到庆幸;此外我们的共同朋友克拉拉•蔡特金允许我的小船打着她的旗帜驶出公海5,我也同样感到庆幸。在那么多“社会主义的英勇而坚决的先进战士们”被大风暴像秋风扫落叶似地扫掉的年代里,这两位妇女的友谊,对我来说是无上的安慰。
梅林
柏林,斯得格里兹,19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