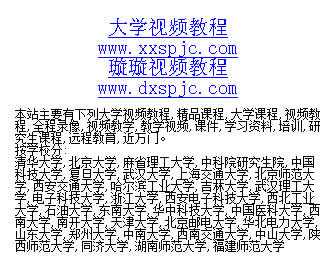![《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著 喜顺儿朗读版[MP3]](http://pic.dxspjc.com/dx_pic/9120412/3608859.jpg)
喜顺儿的声音很好,读的很好;虽然稍许有些静电噪音,却真正是瑕不掩瑜。![《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著 喜顺儿朗读版[MP3]](http://pic.dxspjc.com/dx_pic/9120412/3608352.gif)
![《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著 喜顺儿朗读版[MP3]](http://pic.dxspjc.com/dx_pic/9120412/3608717.jpg)
迟子建,女,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一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万字,出版单行本四十余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踏着月光的行板》,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迟子建作品精华》三卷。
曾获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本书介绍(转贴)
青年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
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它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
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向我们娓娓道来: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追逐驯鹿喜欢的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部落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部落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苍凉的历史长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迟子建始终实践着“用小人物说大历史”这一创作理念。迟子建认为,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只有二十多万字,但作者在里面讲述的却是鄂温克的一个部落近一百年的历史。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题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是关系到人类文化学的问题。在追逐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落、面对其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现状时,可以用 “悲凉”二字形容作者目睹了这支部落的生存现状时的心情。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的。我们为了心目中理想的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达。现代人就像一个执拗的园丁,要把所有的树都修剪成一个模式,其结果是,一些树因过度的修剪而枯萎和死亡。其实,真正的文明是没有新旧之别的,不能说我们加快了物质生活的进程,文明也跟着日新月异了。诚然,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但我们在付诸行动的时候,一定不要采取连根拔起、生拉硬拽的方式。我们不要以“大众”力量,把某一类人给“边缘化”,并且做出要挽救人于危崖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摆布他们的过程。如果一支部落消失了,希望它完全是自然的因素,而不是人为的因素。大自然是美好的,也是残忍的。我们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
《额尔古纳河右岸》有意识地追求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写作这部长篇时作者的激情极为饱满,大约触动了她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作者熟悉那片山林,也了解鄂温克与鄂伦春的生活习性。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问题。当然,其中浸润着作者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它在气象上显得极为苍茫。 (殷红)
 | 点击查看更多 大学视频教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