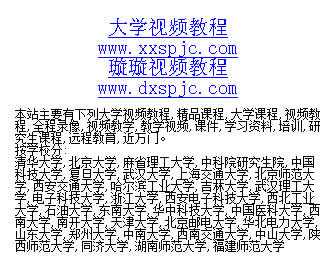![《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The Western Canon)[PDF]](http://pic.dxspjc.com/dx_pic/9090110/1944549.jpg)
编辑推荐
莎 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的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究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 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以崇高的勇气和惊人的学识,《西方正典》充满的激情地向我们表明,某些作家为何能够逃脱那以湮没人类一切成果的时间之遗忘而幸存。它激起我们的希望:那些一直为人性所珍视的东西,仍将为我们的后代子孙所珍视。
——《纽约时报书评》
文学因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魅力和社会工程学的诱惑而被抛弃,当其他都奇怪地陷入沉默的时候,布鲁姆在这部充满刺激力和雄辩力的著作如提出了关于经典的惟一真正问题:“在历史的此一时刻,那些仍然渴望阅读的人将会去读些什么?
——斯坦福·平斯克
这部才华横溢的作品重新激活了西方经典的概念,并使那些最好地代表了这一概念了惊世之作再度进入我们的视野。在阅读文化行将绝迹之时,本书必将赢得有识之士的竭力褒奖。
——理查德·波伊里尔
内容简介
在 女性主义、多元化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非洲中心论等各种新潮理论引领风骚之际,哈罗德·布鲁姆逆流而立,力拒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重申智识 与审美标准的不可或缺。在本书中,布鲁姆高扬“审美自律性”的主张,一仍其“影响的焦虑”理论,以莎士为西方经典的中心,并在与沙氏的比照中,考察了从但 丁、乔叟、塞万提斯一直到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等的二十多位西方一流作家,揭示出文学经典的奥秘所在:经典作品都源于传统与原创的巧妙融合。
本 书为解读数百年来西方伟大作家和重要作品提供了引导,无疑会激发你重温经典的欲望,但它绝不只是一份西方文学作品的必读书目,其中融合了对学识的喜爱和对 审美的激情,才华横溢而又雄辩无碍地维护了一种统一连贯的文学文化,在从往后的岁月里,它将引领我们重拾西方文学传统所给予了阅读之乐。
作者简介
哈 罗德·布鲁姆,1930年出生于纽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1955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早期研究浪漫主义诗歌,曾出版过论布莱克、雪莱、叶 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诗人的专著。除先前提到《影响的焦虑》、《西方正典》之外,他还著有《误读之图》、《卡巴拉犹太神秘哲学与批评》、《诗与隐抑》以及即 将出版的新作《耶稣和亚维:神圣之名》(Jesus and Yahweh:The Names Divine)。作为一个批评家,布鲁姆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后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犹太 教的诺斯替主义与喀巴拉主义则是这些批评的主要对象。在美国,布鲁姆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大牌的学者和批评家。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是“西方 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序方与开篇
论经典
经典悲歌
贵族时代
经典的中心:沙士比亚
但丁的陌生性:尤利西斯和贝亚特丽丝
乔叟:巴思归人、赎罪券商和莎剧人物
塞万提斯:人世如戏
蒙田和莫里哀:真理的不可捉摸性
弥尔顿的撒旦与莎士比亚
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经典批评家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反经典的诗篇
民主时代
经典记忆:早期的华兹华斯与简·奥斯汀的《劝导》
沃尔特·惠特曼:美国经典的核心
艾米 莉·狄金森:空白、欣喜、暗音
经典小说: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和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奇》
托尔斯泰笔英雄主义
易卜生:山妖和《彼尔·京特》
混乱时代
弗洛伊德:莎士比亚式解读
普鲁斯特:性嫉妒的真正劝导
乔伊斯与莎士比亚的竞争
伍尔芙的《奥兰多》:女性主义作为对阅读的爱
卡夫卡:经典型忍耐和“不可摧毁性”
博尔赫斯、聂鲁达和佩索阿:西班牙语系的“惠特曼”
贝克特、乔伊斯、普鲁斯特和莎士比亚
排列经典
哀伤的结语
附录:经典书目
中文版序言
正 如我一些失明的朋友所证实的,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不是一种视觉经验。它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我在这里不是要 做关于阅读的说教,因为那样我就是在对可教者劝喻,而且我有时惟恐会变成有关如何及为何阅读的传道士。英国有一位马克思主义拉拉队的头领竭力鼓噪,要称我 为阅读复兴主义的吉米·斯瓦加牧师。我要是有一点那位不可思议的斯瓦加所具有的奇特能量也好啊!不,我本意不是去重现早年的记忆,那从八岁到十五岁之间的 经历,当时我在布朗克斯图书馆麦尔罗斯分部获得了某种新生。说来难免带有感情色彩和怀旧思绪,因为回忆那七年之久的小读者经历要使我一下子倒退六十五年。 在我将近七十二岁之时,我日益感到自己一生主要的成长经验始于七岁那年,当时我说服了我的两个姐姐带我去公共图书馆,实际上是每天都去。她们已到了可以领 取图书证的年龄。我是家里的老小,一个小调皮,所以她们对我呵护有加,和我一起来回奔走,每人都夹着一堆书。
我记得那里的书借期是两周,并可续借 一次。我最喜爱的诗人有:哈特·克莱恩、华莱士·斯蒂文斯、威廉·巴特勒·叶芝、威廉·布莱克,以及雪莱和济慈等人,我焦虑地盼来四周后还书和借书的日 子,那时我眼睛紧盯着书架上我喜爱的那些书,生怕别人在我再借一次之前把它们取走。我想,正是对这些名篇佳作的极端喜好才激起我对如今屏幕上的东西即电子 书籍之类不屑一顾。我喜欢那些向往已久的书籍的纸张、外观、重量、手感、印刷,甚至是书页空白,如华莱士·斯蒂文斯的《和谐》与《秩序的理念》、哈特·克 莱恩的《诗集》、纳萨奇版的威廉·布莱克作品、叶芝的《最后的诗篇和戏剧》,还有旧的深蓝封面的牛津版雪莱、济慈、丁尼生、布朗宁和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
大 约两年前,大卫·瑞尼克劝我在一场关于“电子书籍”的研讨会上做一次演讲,他幽默却不太准确地把这次研讨会定名为“下载或死亡!”(Download or Die)。我记得自己对一群出版商、编辑和记者们说到,当我们从卷轴书进步到手抄本,再到印刷装订书籍时,那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发展过程。在我演讲并预言 大量投资电子书籍的出版商们会遇到经济灾难时,我的头脑里充满了那些诗卷的可爱形象,那些诗卷伴我度过了童年,成了我幼时周遭乏味环境中的光辉偶像。当时 我的左邻右舍都是东欧移民和他们的孩子。我们在家里和街上都说意第绪语;而我在五岁半上小学前从没听过英语。作为一个极少耐心的读者,我有着疯狂的阅读速 度和记住任何我所喜欢的东西的超凡能力。我是自学英语阅读的,当时还不知如何发音。所以直到今日,我的语音仍有自己独特的腔调,我通常更多地依赖眼睛而不 是耳朵。
也许你们已经知道,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我对自己专业领域内所发生的事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因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 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 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如果我是 出生在1970年而不是1930年的话,我就不会以文学批评家和大学老师为职业,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赋也不会作此选择。但是,正如我在一些完全乱套的大学 中对怀有敌意的听众所说的,我的英雄偶像是萨缪尔·约翰逊博士,不过即使是他,在如今大学的道德王国里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
我对布朗克斯公共图书 馆麦尔罗斯分部记忆犹新的是,那些藏书中的核心部分都是基于审美和认知的考虑而遴选的。如果我不是在1938年而是在1998年怯生生地在那里跌跌绊绊走 动的话,那我会发现有什么东西可用来陶冶自己呢?三年前,当我在政治正确的斯坦福大学于一阵骚动之后开始讲座时,我学会了对这类事情略加防范,所以如今我 也注意避免冒犯这里的任何人。在斯坦福讲演是我在耶鲁以外的大学里最后一次露面,我说,如果一张桌子或书桌在运输途中脱落了几条腿,购买者是不会不要求退 款的。而我们这些人现在在斯坦福以及其他地方却要得意地向人们推荐或布置阅读那些已经掉了腿的书籍,仅仅是因为这些称不上是书的读物是由一些有特殊身份、 性别、性欲倾向和族裔背景的人所写,或是涉及到那些流行于学界和媒体的憎恨政治中的东西。我不认为自己的言论有任何政治色彩。在这个宗教战争不断的年代 里,我们有一位总统正在统治着我们,他曾吹嘘说自己从没完整地读过一本书。于是,在对靠掉书袋而写成的书大加赞扬的人和自诩半文盲的领导人的崇拜者之间, 你几乎是别无选择。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各家图书馆也难逃此劫。我被一再地告诫说,孩子们读什么无关紧要,只要他在读书就行,不管他读的 是哈利·波特还是斯蒂芬·金。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因为学着去读《哈利·波特》会使你进而要去读斯蒂芬·金的小说,这也正是后者在评论最新的《哈利·波 特》时得意地宣称的。这篇评论发表在反文学的《纽约时报周日书评》上。
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难以逆转。媒体大学(或许可以这么说)的兴起,既是我们衰落的症候,也是我们进一步衰落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