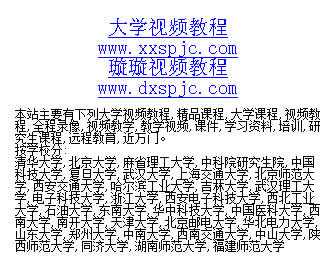书名:清国史
编者:清国史馆
卷册:十四册
大小: 1.28G
清晰度:中高可辨
介绍:《清国史》,中华书局于1993年出版,由十一个本纪、十四个志、一万四五千人的传记组成。人们知道它,是近两年的事,相信以后它将越来越为读者所了解。本书作者在图书馆浏览它,所读不多,有待于来日补课,现就印象对其绍述一二,并与《清史稿》有所比较。

(1 )清国史馆的著述汇编
清朝国史馆负责王朝历史的编纂,写作纪、志、表、传诸种体裁的史书。此系日常工作,必须不断地进行,即一个时期的某种史书完成,经过御览,成为定稿,过一段时间,再奉命续修一部,这样就形成若乾种不同体裁的史籍,但是在一个王朝延续期间内,国史馆不会编纂纪传体的王朝史,换句话说,国史馆所写成的只是纪、志、表、传分体的著作,不会有一代王朝的全面通史,而这一类著作,通常是下一个王朝为被其取代的前朝去作,所以清国史馆不可能写出有清一代的纪传体通史,《清国史》不会是一部完整的清史,而只可能是具有该王朝历史的分体的书稿。这样说,固然是根据修史制度而言,更重要的是现存《清国史》的实际状况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的。
《清国史》的本纪,只写到同治朝,光绪朝的未完成,仅有资料长编的“编年”,宣统朝则付诸阙如。况且各个本纪正文前均置有《凡例》,与二十四史本纪的不载凡例有别。
《清国史》有“志”十四种,各志体例不一,名称不统一,所叙述的时间长短不一,质量参差不齐,《艺文志》、《皇朝职官志》、《天文志》等开篇有《修辑凡例》,《选举志》、《舆服志》、《皇朝刑法志》等则没有凡例,志多有序,而《仪卫志》,既无凡例,也没有序言。在志的名称上,有的又冠上“皇朝”字样,可见其不规范。而且这一名词的使用,可能标志刑法志、职官志都是独立成书的。至于各志所反映的时代内容,起始都是清初,不存在差异,但截止年份则全不一致。《皇朝职官志·修辑凡例》云:“沿革载至嘉庆二十五年止,此后复有更定者,俟续纂时增入。”(第4册第760页)直接了当地告诉读者,它仅记录嘉庆朝以前的官制,不可能指望它能提供道光以降的官制情况。《艺文志·修辑凡例》云:“艺文志,旧五卷,今续辑为八卷,首二卷。”(第4册第739页)新、旧志各系何时所修,本书作者尚不知晓(旧志疑为乾隆朝或前此所修,新志疑为嘉道时修纂),但从中可知艺文志有过两次编写,后一次也是例行修纂,非为总结有清一代之艺文。《皇朝刑法志》系按朝年编写,起于顺治朝,止于嘉庆二十五年。《选举志》对于光绪后期的废科举、兴学校,无所反映。《天文志》、《乐志》也都说的是嘉庆以上的事。这些现象表明,各种志书兴修时间不一,续修情况不同,出现在《清国史》的时代面貌就不统一了,而没有写到清末,则是共同的。
《清国史》的传,更是不断地编修,体例也不尽相同。《国史宗室王公传》卷首,包含谕旨、圣制文、圣制诗各一份,谕旨系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上谕,圣制文为嘉庆帝所撰。以上谕、御制文开篇,是王公传已构成专书,但这种卷首不合纪传体史书的列传体例。大臣传分出正编、次编、续编、后编和新办大臣传数种,儒林传由儒林全传、儒林传、儒林传后编三部分组成,忠义传内含正编、次编、续编、后编和国史忠义划画一传档现办、新办已进、新办未进七个部分。名称的差异,说明修纂的时间不同,其《新办国史大臣传》含有五百余人的传记,人物首起李鸿章、阎敬铭,终于张之洞、黄忠立,是咸同光时代的人,篇幅很多,印了整整一本书,可是未作分卷,显然是未定稿。忠义传的现办、新办已进、新办未进,从名称已可知是未杀青之作。所写人物的生存时间,以《后编》说,计有六十卷,每卷目录前写明传主死事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其第五十三卷云:“同治五年至十二年在贵州剿苗匪阵亡。”最后一卷谓:“光绪八年九年以剿办贼匪积劳病故。”可知传主生存期不晚于光绪。《忠义传新办未进》最末一人为赖高翔,咸丰年间死事于江西广信。所以进入忠义传的传主多是生活于光绪前期以前的人。
上述诸种情形,使人对《清国史》产生的印象是:体例上不完全符合纪传体史书的规范;各部分文字形成的时间前后相差甚大,且无统一修订;从而内容不完整,清代后期的许多制度、事件和人物活动没有反映;写作目的是为本朝(清朝)作历史记录,是颂扬朝廷盛德和表彰臣工,但在客观上为异日完成一部王朝史作出了多方面的文献准备;这些文献含有纪、志、列传等文体的专门著作,因系国史馆所制作,并为其所保存,甚至它们可能置放于一个专类档案中;归结而言,现在问世的《清国史》是清朝国史馆陆续纂写的纪、志、传诸种文献的汇集,原来并非一部书,只是今人将那些置于一处的成部和散篇著述汇合在一起印成一部书。因本书作者所掌握的信息甚少,不知所说是否有点道理,殊不敢自信,书此以求教于方家。
(2)抄录与出版
清国史馆的诸种著作,当北京清史稿修书时被从原来的库房调出,作修史参考。近代有名的藏书家、嘉兴刘承乾闻知清史馆有清朝的历朝实录和本纪、志、传,就商于馆长赵尔巽,愿赞助该馆经费,请其倩人代钞上述诸书,双方达成协议,于1923年钞出历朝实录和《宣统政纪》,而“《清国史》传钞,始于1924年夏,完成于1928年夏,前后历时五载,其间以钞费挪用、史馆易人、政局动荡等原因,钞书曾经中断,若非刘氏力促并增付酬金,《清国史》传钞几于功败垂成。”(吴格:《清国史影印说明》)钞成之后,刘氏将《清实录》和《清国史》视为珍贵秘藏,虽在抗战动乱期间,亦随身保藏,未受损失。迨至五十年代中,《清国史》转让给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
九十年代,复旦大学图书馆与中华书局编辑部合作,将刘氏嘉业堂钞本影印,为省篇幅,取缩印法,排为上、下双栏,并添印边栏,新编页码,分装成十四册。以上说明,参阅吴格文,兹将该文附录于后。(【附录11,6页】)出版者还制作《清国史本纪传人名索引》,收录纪传(本传、附传)人名一万五千余条,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另附笔画索引,人名下注出传文所在卷名、卷次,在影印本的册次、页次及上、下栏。
(3)《清国史》的卷目
卷目反映内容,本书不拟对《清国史》的内容作全面绍述,故对卷目略有所陈,读者自可想见其内容概况。
本纪,自太祖朝起,迄穆宗朝止,其中高宗朝分量最大,达六十二卷,此不足怪,而穆宗朝次之,有五十四卷之多,大约是有所谓同治中兴的缘故吧。另有德宗编年。
志,有十四个项目,食货志、地理志篇幅均在二百卷以上,而仪卫志、舆服志、河渠志皆各四卷,选举志也只有六卷,所以各志内容多寡颇不平衡。
传,含有王公传、大臣传、循吏传、孝友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究竟全书内容概貌如何,请看其总目。(【附录12,2页】)
全书的内容,以传记最多,约占该书的四分之三篇幅,志有二百余万字,与其他纪传体史书一样,本纪的分量略少些。
《清国史》缺少通常纪传体史书所应有的“表”这一大类;本纪无宣统朝;与《清史稿》相比,志类少灾异志、交通志、邦交志;传类没有列女传,至于不像《清史稿》有畴人、艺术等传的名目,但在文苑传含有这方面人物。
(4)传记史料
《清国史》的传记还不能称为第一手史料,因为它是有所本而作,且其所据的传文,有许多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但是它对于《清史稿》而言,则是后者的史料来源之一,在这种意义上说,它又可称作第一手资料,于此可知其史料价值之不一般。
全书各传所收人物,总计达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四人,数量之巨,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史稿》可谓鼎足而三。前已说过,《清史稿》舍弃了清国史馆传记一千二百份,于是在《清国史》中的人物传记,《清史稿》少的甚多,如第十一册的《新办国史大臣传》中的文秀、容贵、广忠等人,在《清史稿》里没有传记,连顺无传,仅在表里有其任职的记录。第十一册《循吏传》卷六有白云上传,《清史稿》无,可能因其为武官之故;卷十一有沈鎔经、李景祥传,《清史稿》亦无;卷二有蒋伊传,《清史稿》无传,仅提到他一点事。第八册的《大臣画一列传次编》卷133有李清芳传、谢溶生传,《清史稿》皆无传,也是在部院大臣表里出现他们的任职。是否他们没有可以叙述的史事呢?亦未见得。李清芳,乾隆元年进士,五年任监察御史,次年以捐例既停,建议未授职的只给职衔顶戴,停其铨选,乾隆帝以他不识大体,严加申饬;次年,以夏灾例不赈济,而影响夏种秋收,要求给予赈济,得到批准;九年奏请宽奉天等处海禁,亦获准行;同年奏大臣等保举主考人员四十九人,江浙两省占二十人,而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五省无人,不无有弊,请对被举人员进行考试,乾隆帝认为他因不在保举名单,怀私而有此议;十年湖广总督疏请将捐监事例的捐粮改为捐银,李氏认为不妥,恐遇荒年无粮赈济,皇帝采纳其议,不作更改;同年,以秋审情实案犯过多,有伤好生之德,乾隆帝以其所见迂谬,严予申饬;十三年升刑科掌印给事中,二十年迁兵部右侍郎,二十二年因一个九卿会议中的错误,降二级留任;两年后,以其父年老,命其原品休致,回籍侍养。李氏身为言官,履有奏议,虽有对有否,尽了言责,是有事可写的。其事详见附录。(【附录13,1页】)谢溶生,乾隆十年进士,十三年授职编修,二十年擢侍读学士,提督山东学政,奏各学增广生俱有定额,应及时补充,不得压积,得到乾隆帝赞同;二十四年调江西学政,次年参奏江西巡抚阿思哈婪贿派累,经皇帝派尚书前往,查实治罪;二十六年密奏童生李雍和狂悖事,乾隆帝以其不同疆臣合作,怀私邀功,传旨申饬;三十三年任太常寺卿,奏所属赞礼郎、读祝官由监生、官学生出身者保送抚民同知、通判,亦照理事同知、通判例,历俸三年,方准保送,得旨允行;三十八年署礼部尚书,寻被参大祀时偷安不敬及失察家人索诈,革职,发伊犁效力,五十五年释回。(【附录14,1页】)事迹不是很多,也还是有一些。《循吏传》卷十一沈鎔经传,传主为同治七年进士,九年任江西贵溪令,次年以获盗出力,下部优叙;十二年调上饶知县,逮捕以吃斋为名聚众谋反的民众首领;召健讼诸生读书官舍,使他们感愧知自爱;官至广东布政使。同卷李景祥,光绪二十一年进士,任奉天广宁令,处理传教士、教民与百姓的争执较得体,对光绪二十六年俄国侵略军与土匪勾结、二十八年当地六和拳再兴的事务,作出处断。(第12册第227页)《清国史》中一些传记,写得简单,基本上是履历加一点事情,如《新办国史大臣传》的寿昌传,除了他从笔帖式,升至兵部右侍郎的履历,只写了两件事,一是同治帝死后,随同礼亲王世铎等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二是当崇厚与俄国议和失当议斩时,奏请量予减等。(第11册第97页)同类传里的巡抚邵友濂传,履历而外,内容更是贫乏。(第871页)
《清国史》与《清史稿》同有的传记,互有详略,不可偏废的情况,亦存在着。《清国史·宗室王公传》卷十延信传,写传主于康熙五十七年随从抚远大将军允
题西征,五十九年为平逆将军,进军西藏,平叛立功,晋封辅国公,雍正五年以二十大罪被幽禁。写其立功事有实迹,二十罪状则一一列出。(第5册第126页)《清史稿》卷219 延信传,对《清国史》的上述二事记之不详,但择录了康熙帝对他的褒扬诏书。(第30册第9048页)所以两书的载笔互有详略,大学士蒋廷锡的传记同样表现出这种情况。《清国史》对其在康熙朝入值内廷,随从康熙帝巡幸,受宠信,以及雍正八年皇帝大病时参与处理机密事务,都有记叙,(第5册第1042页)而《清史稿》对此忽略,全然没有涉及,但记录他对加强府县学教育的建议。(34册第10250页)这种互有不同重点的叙述,作为一本书不是好事,然而见于两部书,则是互为补充了。
《清国史》的传记,大多写到光绪前期的人物,而《清史稿》则写至清朝终结,加之内容的互有详略,所以两书具有互补性,那一部也不能取代另一部,因而都不能废弃。读者可以根据需要将这两部书结合着阅览。
(资料来源:《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