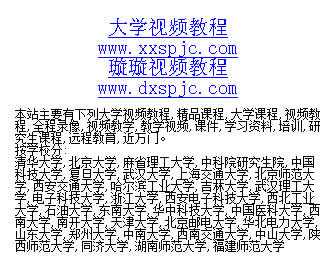故事描述:一个英国的十几岁的小混混亚历克斯被警察送进了监狱。在那里他为了缩短行期,答应把自己当作小白鼠一样送去为一项叫做“厌恶疗法”的充当实验品。这项计划是政府为了在监狱里腾出位置给政治犯而提出的。通过“厌恶疗法”,狱警们认为亚历克斯的暴力倾向总算是被“治愈”了,于是亚历克斯被放了出来。但是出狱后的亚历克斯发现自己被旧朋友们所屏弃,连家人亲戚都不愿意接受他,而他本人也并没有放弃暴力。最后,垂死的亚历克斯成了以他为成功范例大力鼓吹的政府的一个大伤疤。他伙同一群同伴一起冲进了一个小说家的住所:他写的书(名为《发条橙》)为政府使用荒唐的“厌恶疗法”辩护鼓吹。
![《发条橙》安东尼·伯吉斯(A Clockwork Orange)[MP3]](http://pic.dxspjc.com/dx_pic/6072409/2042979.jpg)
题解:clockwork 是时钟的发条,是让时钟走得准确的装置,所以如果走(跑)的像时钟发条般准确,即表示“机器运作的很好”,或“事情进行的有条不紊”。还有一个相近的词clockwork orange(发条橙),老伦敦人用它作比喻,总是用来形容奇怪的东西。“He is as queer as a clockwork orange他像发条橙一样怪”,就是指他怪异得无以复加。
小说最初在美国发行的时候,发行商坚持将小说描写亚历克斯长大后最终放弃了暴力,并结婚生子的最后一章删去了。而伯吉斯始终对这一章耿耿于怀,认为没有这一章,他的思想就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因此,他一直不满意美国版的《发条橙》,不管小说或是电影。因此本站提供给网友为《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英国版本。
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历来是争论的焦点,而争论多缘于对其中宣扬的性和暴力。当时,该片曾因为其中的性和暴力而被禁播,然而,性和暴力难道就是该片的全部么?欣赏这部电影的时候,把性和暴力作为一个切入点,这样的做法和那些批判该片禁映该片的卫道者也没什么区别了。
发条橙是一种玩具,上了发条,就会自动的转动的一个橙子。该片以此为题其实透露了库布里克的某些想法。曾有人对我说,“人人都是上帝手中的一直不停转动的发条橙”,我想,控制这只橙子的“上帝”还包括社会,从这部以发条橙为题的影片里,我也看到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社会本位的妥协。
最初,不得不承认,阿里克斯是个绝对自由的人,他享受着自由,听自己喜好的音乐,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任由自己的意志行事,及至的享用着自由,然而,人是处在社会中的,啊里克斯行使自由的同时,却侵犯到了其他人的权利。按照洛克“政府契约论”的原理以及西方天赋人权的理论,每个人都自由、平等的享有权利,这些权利是生来就赋予的。然而,及至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往往会侵犯到其他人权利的行使,为了协调这个矛盾,于是每个人把自己的权利让夺出一部分,形成一种公权利,由这种公共权利来惩治暴力,抵御外来侵略等等,而公共权利的形式造就了军队,法律,警察等国家机器的产生。阿理克斯自由的发泄自身暴力和性的需求的同时,却伤害了他人家庭和生存的权利。这样的行为触犯了社会游戏的规则----法律,因此,他锒铛入狱。
为了减短刑期,阿里克斯自愿得接受了“罪恶改造疗法”。通过这种疗法的治疗,他变成了一个不会反抗,没有性欲的“良民”,放弃了自身的权利。无异议的,这样一个“良民”是最适合社会平稳、安定发展的需要的,如果一个社会里所有的公民都是这样的“良民”,社会的统治者也最希望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良民”,来维持统治的长治久安。接受这种疗法,其实也是阿里克斯放弃自身权利,向社会的妥协。而且规则并不是这么简单,对社会的统治进行侵害,自然会遭到社会的报复。每个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负责,14年的刑期缩短至两年也不能够抵消阿里克斯原先的罪恶,犯罪惩罚规律的同时还潜在着另一种规律的运行----复仇。
人类历史的悠悠长卷上,复仇曾普遍并且长期存在。以复仇为主题的故事仍一如既往地感动着今日的受众——从西方古希腊的《安提格涅》、《赫库帕》,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乃至近代名篇《基督山伯爵》都涉及了复仇这一题材。而在东方的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似乎都发生在先秦时代,着名的如伍员鞭尸、卧薪尝胆、荆柯刺秦王以及本文用以示例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数十年来中国两部享有盛名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在淡化其“革命色彩”之后,仍然讲述的是复仇的故事。此种报复性反应,是生物学的正常现象,是任何一种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和本能。虽然就有些人看来,这种反应是“蜗角之争”,但它却是长期经过自然选择的生物存活下来的竞争基因,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承袭了这种基因。尽管由于种种理性原因,这种本能受到某种程度的弱化,或者被有意淡化和压制,但它还是存在于生而为人的生物本性中,难以消失。出狱后的阿里克斯便遭受着疯狂的报复。戏剧性的巧合,他一一遇见了原先他所伤害过的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都对他进行了报复。因为阿里克斯这样没有攻击性的良民,也使得渊源相报终止在他从阁楼跳下那一刻。
而且阿里克斯自戕的行为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划上句号,如果故事至此终结,那全片的主旨该定论为:你侵害的社会,必定要招到社会的报复,你做错了事,就该为自己的错负责。全片的基调也该变为爱国主义,爱社会的教育影片。库布里克当然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于是发条橙便有了个戏谑的结尾。为了挽回选民的信任,反驳亚历山大等在野党人的批评,内政部长亲自到医院看望阿历克斯,代表政府表示歉意,并为他今后的生活做了妥善的安排。经过治疗,最后阿历克斯恢复本性,享尽淫乐。看似代表社会的统治者向阿里克斯进行妥协,让其通过治疗恢复原来所有的个性,看似社会本位对个人本位的低头。其实,阿里克斯所扮演的,仍然是政治上的一个利用品。
说到这里,不难看出,阿里克斯除了入狱前挥霍自由,享尽权利那段时间以外,他都是被社会所操控着,为了宣扬某种可以缩减监狱开销,经济改造的疗法,他参加治疗,为了统治者维持统治,他又一次的接受治疗,经管他的年轻,个性鲜明,但他所扮演的也不过是一只社会所操控的发条橙子。其实,被社会所操控的发条橙又何只阿里克斯这一个典型呢。
发条橙与潜伏危机[左岸右边]
《发条橙》不仅是一本奇异的书,也是一部怪异的电影。书的作者是:安东尼.伯吉斯。英国现代作家。电影的导演则是斯坦力.库布里克。美国着名导演。巧合的是,这两位大师都是独断独行的人。伯吉斯崇尚的是“自由意志”而库布里克在好莱坞则被称作最不合作的人。在他们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联系,这便是《发条橙》。无论是书或电影都被一种论调评价着——争议。
一、 两只《发条橙》
以前,中国曾这样评论西方电影:毒草。而对如今而言,无论中国或是外国,都把〈〈发条橙〉〉看作是“毒草“。
原着〈〈发条橙〉〉中的主人翁是以“我”在文中出现的。“我原是一个生活在后现代英国的叛逆青年,在我15岁时无恶不作,我与三个好友到处闹事、打架、甚至强奸和杀人。后来我被朋友出卖,被关到了监狱中,为了提前出狱,我接受了一项政府提出的特殊治疗,在出狱后,我无法作恶,因为每当我想到血腥与女色时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恶心感,当我回到家后,我的房间被父母的养子占去,而我在街上流浪时也倍受欺凌。我失去了选择生活的权利,最终我在最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从窗口跳下。当我醒来后,我竟痊愈了。变成了原来的我。可以选择思想与爱好的我。但当我看到当年与我作恶的朋友后,我发现自己是必须长大的。我需要一个家和一个孩子。于是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
电影版的〈〈发条橙〉〉与原着情节基本相同,但却删去了痊愈后“我”的改变。应当说,电影版的〈〈发条橙〉〉更令人不寒而栗。它不仅是对政府专权的抗议,而更深层的去挖掘人的本性。这让我想到一个词语——失效。是的,正是这“失效”的必然让“我”在电影末说出了那句“我痊愈了”。让妄图用科技改变人类道德选择能力的专制者们认清了自己的有限、有所不能!
鲁迅曾嘲笑中国文化不敢面对悲剧的事实,这又何尝不是人性中对善和美好的渴求的表现呢!不过是太软弱了,你不去面对,它还是存在的,还是发生作用的。我的心隐隐作痛,我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人性中恶的问题。即使它遵循了“自由意志”的愿望,但它毕竟是恶的,而且它将滋生于我们不断前进的文明之中。我们无法改变却也难以逃避。我们只能在历史发展的规律中让自己适应社会的改变。让人类的道德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罢了。
由此,不难看出,〈〈发条橙〉〉的主题是严肃的。但却用了超现实的表现手段。这是否在暗示,道德在社会中所潜伏的危机呢?
二、 发条橙的意义
首先,我们在理解本文的题目上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发条橙不同于发条西瓜或发条苹果。在马来语中“橙”的意义与“人”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发条橙要表达的是像机器一样的人。当主人翁有作恶的人变成了被害的人时,他便是我们所说的发条橙。此时的他,没有道德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就像失去了灵魂。
试想,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对待社会态度选择的权利,我们是否也会变得像一台机器呢,或者是一台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的智能机器?当然,或许作者的想法过于悲观,而且对于社会的发展怀有不安,但,由现在的发展方向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越发机械化。简单的概括也就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所要面对的一个空前巨大的问题。它的解决与否很有可能关系到今后人类的命运。如果处理不当,我们都无法保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毁灭人性,最终在进化中的退化,成为一台台杀人与战争的机器,或者说,一只只吃人的动物。
因此,〈〈发条橙〉〉不只是另类的代表,它更是以现实发展作为基础的。
死亡、性、暴力、虚无荒诞、尽现其中。我认为它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感受力,和面对某些问题的勇气。“它源于20世纪以来那种文化解体的经验,尝试对这文化解体带来的不定性、虚无性及社会的控制性加以反省和理解”。这种问题意识的凸显是人对自身和社会反思的表现。我们庆幸能够有人提醒,同时也希望我们真的能够觉悟。
〈〈发条橙〉〉中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似乎还在用那种高亢与激奋告诉我们主人翁对生活唯一的信心,而不自觉中,电影和书也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细味。在科技、知识、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否也正在步入〈〈发条橙〉〉中那个“后现代”的超现实时代呢?如果是,那我们或许应该为自己的未来作些努力了吧。
潜伏的危机无所不在,它甚至在等待某根导火线被人类自己点燃,我们正像高度文明奔去,但同时,我祈祷,人类不要被自己毁灭。
《发条橙》:电影和小说[阮一峰]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是先看电影,然后再去读小说的。记得看完电影的时候,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但是又说不清震撼我的到底是什么。现在想起来,好象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的电影都不是一眼能看穿的,似乎有一种伪装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为了把这部电影搞明白,或者说“看懂”它,我找来了原着,认认真真读完了,两者一对比,这才对库布里克的表现手法有所领悟。 小说《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并不长,薄薄一册,十万字,两个晚上就读完了。原着一点也不晦涩,情节性很强,表现的主题“人必须有道德选择权”也不算新颖。唯一的难点是作者自造的Nadsat语言,但在中译本中,语言难点自然就不存在了。我的感觉是,从文学角度看,这部小说不能算是第一流的作品。但电影就不同了,经库布里克之手呈现出来的视觉形象是那么令人难忘,以至它成了二十世纪中一部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那么,库布里克成功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电影对小说情节的改动并不大——除了没拍最后一章,这个我在后面会详细谈——基本上是忠实于原着的。“忠实”的意思是,导演不曾“深化”或“浅化”小说的主题,更没有变造主题,电影是原原本本的把小说搬上了银幕。库布里克的创造不是表现在电影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电影中那些千奇百怪的视觉画面中。 《发条橙》是一个充满了暴力和强奸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在无人的街道、空旷的大宅、监狱和精神病院之类有很强现场感的地方,这些场景在小说中也许只是几个平淡无奇、一笔带过的单词,但如果落实为电影中活生生的画面,效果就有些惊世骇俗了。库布里克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把这些镜头毫无顾忌地都拍出来了,比如同样是表现暴力,大多数影片是将镜头对准了施暴者,而《发条橙》始终是拍受害者,血流满面、蜷曲翻滚、呻吟不已;再比如,《发条橙》里的强奸就是这件事原来的样子,毫不隐讳,而不象某些影片中只看见晃动的人影,配上几声女子的惨叫。所以在这一点上,电影是借了小说的光的,小说本身就提供了有视觉冲击力的故事基础,供库布里克大胆发挥,但库布里克最大的创造还不在这里。 看过电影《发条橙》的人,恐怕对开头的画面都很难忘怀吧。先是一个主人公亚历克斯的特写,他戴着圆顶黑礼帽,脸上狞笑着,右眼的上下方都贴着夸张的假睫毛,袖口上装饰着带血的眼球。然后镜头逐渐拉长,露出亚历克斯的全身和他的三个伙伴,他们都外穿着白色的紧身内衣,内裤套在最外面,以显示自己的性感。他们正坐在柯罗瓦奶吧中,品尝着奶茶。黑色的奶吧里亮着几盏冷光灯,四周装饰着各种颓废的艺术品,所有的桌子和椅子全做成了裸体女人的样子,比如吧桌的四条腿是女子的两手和两脚,桌面则是她的胸脯。我看了这个形式感十足的开场后,立刻就想到了毕加索和达利的一些作品——变形、夸张、鲜艳、对比强烈——再看下去,才发现整部影片都是这种风格,几乎每一个布景都很奇特,有一种未来主义的味道,仿佛是搬上了银幕的现代派绘画。我来举几个细节,影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都头戴奥纶的彩色假发,亚历克斯住处的窗帘上印着贝多芬硕大的头像,而在监狱的入狱处居然平放着一排陶瓷浴缸。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新奇怪诞的场景让我有一种好奇感,急切得想看下去。后来我读小说的时候,看到某一个情节,眼前就不由自主浮现出电影里的样子。我想这是大多数人的体会,库布里克为《发条橙》找到了外形,如果没有这些奇特的布置,电影是决不会这样成功的。 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库布里克要这样处理这些场景,或者说,他为什么要这么拍。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这些场景确实与主题的关系不是很密切。我猜想的答案是这样的,首先库布里克想强调这是一个假想的故事,这不是现实,所以用这些布景提醒大家这不是真的(但影片里有纳粹和伊丽莎白二世的标志,这说明他也不希望这个故事和现实完全无关);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重视影片的形式和视觉效果一贯就是库布里克的风格。库布里克是那种喜欢华丽新奇的导演,平平淡淡不是他的追求。本文开头,我说库布里克的电影有一种伪装,就是这个意思。仔细想想,他的其他主要作品《2001漫游太空》(2001: A Space Odyssey)、《闪灵》(The Shining)、《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最后的《大开眼界》(Eyes Wide Shut)等等,莫不如此,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独立的外表,而内容隐藏在外表之下,反而倒有些看不清了。库布里克得过的唯一一个奥斯卡奖就是视觉效果奖(顺便提一下,《发条橙》得到过1971年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剪接和最佳剧本四项提名,但最后都输给了《法国贩毒网》)。库布里克如此喜欢形式,也许和他早年当过杂志的摄影记者有关系。 我以下想谈的,也是历来争论最大的,就是如何看待电影缺了最后一章。小说最早在英国出版的时候,共有21章,后来在美国出版却变成了只有二十章。库布里克的电影是根据美国版拍的,所以等于是只拍了前二十章。原作者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1919—1993)对此大为不满,嘲讽道: “《发条橙》拒绝被忘记,这主要归功于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同名电影。我自己非常乐意与它断绝关系,可惜做不到。……我的后半生有大量的时间在复印关于创作意图和意图落空的声明,而库布里克和纽约的出版商却在恬不知耻地享受肆意歪曲带来的回报。” 为什么作者认为少了最后一章就扭曲了创作意图?电影和小说两个版本从主题上分析,哪个更好呢?为了说清这个问题,先让我来补述一下第二十一章的内容,也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发生的故事。 电影讲道,英国政府决定在亚历克斯身上建立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使他一想犯罪,就痛苦不堪,以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结果反对党拿此事大做文章,令政府狼狈不堪,最后不得不替亚历克斯解除了原来的设置,使他又可以随心所欲的犯罪。亚历克斯说了一句“我已经全好了”(I was cured all right),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了。第二十一章接着往下写道,亚历克斯又和以前一样,组织了一个犯罪团伙,实施抢劫和强奸,但现在他的手段更高明了,再也没有被捉住过。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这种生活感到了厌倦,渴望结婚成家,于是就放弃了犯罪。 我不知道别人对第二十一章怎么看,会不会有人认为它只是把以前的内容做一个同义重复?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和小说的主题大有关系。作者的意思是人必须有自己的选择权,善和恶都必须出于自己的选择,“强迫行善”和“强迫行恶”是一样不能被允许的,否则人就不是真正自由的,而只是一只发条橙了,“硬是强迫生机勃勃、善于分泌甜味的人类,挤出最后一滴橙汁,供给留着胡子的上帝嘴唇。” 电影只拍到政府又把亚历克斯变为正常,这等于说亚历克斯仍是一只被动的“发条橙”,他仍在外力、而不是在自我的控制下。小说中的第二十一章就不同了,这一回亚历克斯放弃犯罪是在自我的愿望下实现的,所以最终他恢复了人的力量,不再是“发条橙”了。很明显,小说的结尾更光明和圆满一些,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又回到了现实”,而库布里克的电影则“只是一个寓言”。 我仔细想过这两个结尾,觉得含义确实大不一样。但我也说不出哪个更好一些。好在每个喜欢电影《发条橙》的朋友,都乐意去读一下第二十一章,同时接受两个结尾,也许这比接受任何单一的结尾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