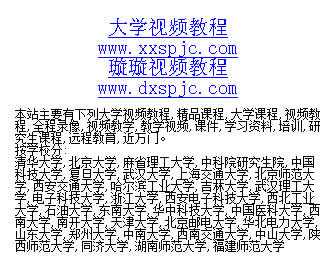![《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未删节版[MP3]](http://pic.dxspjc.com/dx_pic/6012404/0627431.jpg)
马克·吐温是美国人民最喜爱的作家,他的作品广为流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下简称《哈克·费恩》)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1884年这本书出版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从那时起一直吸引着公众,在所有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它是译成外国语中最多的一部。纵观美国文学,自欧文以来,精品华竟,浩如烟海;名家巨擘,灿若群星。各种类型的小说同时并荣,杂然纷陈,形成一种令人目不暇接的多彩局面。其中,开一代文风的艺术天才马克·吐温独树一帜,以对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对儿童心理的深刻揭示和精彩描写,塑造了性格鲜明、永不晦谙的艺术形象,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哈克·费恩》就是这样一部杰作。它被誉为第一部以“地道的美国话”写成的伟大作品,影响了从安德森、海明威、福克纳到赛林格及至80年代成名的美国小说家温斯顿·格卢姆等几代作家。它像水势浩淼的密西西比河,滋润着丰富多彩的美国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海明威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崇高的评价:“这是我们创作的最好一本书。所有的美国作品发源于此: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克·费恩》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匀称的场面组合。整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形成对称的模式—在陆地和河流上。这两个场面交替出现,将哈克的冒险有机地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故事是以哈克在陆地上的生活开始的,最后又以他在斐尔普斯农场的经历结束。有趣的是,哈克对陆地及其所谓的文明并无多大的兴趣,整天想离开这块文明的土地,回到自然的怀抱。这与马克·吐温本人的经历不无关系。他留恋工业社会以前的乡村生活,痛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病。1882年回到密西西比河时,他看到的并不是记忆中童年的乐土,而是到处都有现代工业的影子。哈克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似懂非懂地认识到,在道格拉斯寡妇的关照下,他得不到任何乐趣与自由。“道格拉斯寡妇拿我当他的儿子,说是给我受点教化。可那寡妇一举一动都很讲究规矩和体面,实在太闷气,在她家里一天到晚过日子真是活受罪;所以我到了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偷着溜掉了。我又穿上我那件破烂衣服,钻到我那空糖桶里去呆着,这才觉得自由自在、心满意足。” 那个空糖桶是一道墙,象征性地将哈克的世界与道格拉斯寡妇所生活的文明世界隔开。当时,现代文明社会束缚了哈克:“他不得不用刀叉吃饭,还不得不用餐巾、杯子和碟子;他还得念书,还得上教堂作礼拜;谈起话来总是斯斯文文,以至语言在他嘴里变得枯燥无味;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文明的栅栏和障碍物老是把他关在里面,连手带脚捆绑起来。” 忍受不了这些规矩的约束,哈克躲进废弃的屠场后面的空糖桶里。汤姆在那里找到了他。哈克只有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才觉得快活开心。他为什么不喜欢这个文明世界呢?这就是马克·吐温创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揭露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
十九世纪的美国,特别是西部,到处充满着欺诈和凶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金钱关系。货币作为物与物之间交换的媒介,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到了金钱社会,它变成了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筹码,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如果说,作为一个“自由”白人的哈克,是为了摆脱父亲的暴虐管制和传统教育枷锁去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话,那么,吉姆从一开始逃亡就是因为不堪忍受黑人沉沦人间地狱之苦,为了反抗罪恶的蓄奴制。作者以白色描写真实,精雕细刻的手法,通过生动而具体细节对这一人物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塑造。把他刻画成一个令读者感到真实亲切的有血有肉的人。作为自幼囚于“主人家”的奴隶,一个饱受倒悬之苦的黑人,他有愚昧,迷信的一面,竟至达到荒诞不经,十分可笑的程度。他用从牛胃里掏出来的笔球算卦,还想顺便骗几个钱花;调皮的汤姆趁他晚上坐在树下睡着的时候捉弄他,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挂在了一根树枝上,吉姆醒来后把这事渲染得神乎其神,添油加醋地说是妖巫们骑着他游遍了世界,然后把他的帽子挂在了树上等等。他为自己这番胡编的“经历”而得意忘形,竟至不把别的黑人放在眼里。但是出逃后的吉姆,在种种为争取自由而经历的千难万险之中,却显示出他有着高尚的品德和纯洁的灵魂。他是黑奴,但并不逆来顺受,听凭白人的摆布。他在思想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具有与蓄奴制相抗争的顽强精神。他不承认蓄奴制是天经地义的,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享受自由生活的权利。他渴望着自身和老婆孩子的自由,但并不是一味考虑自己而不顾他人。在逃亡途中,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哈克;为了让汤姆治伤,他宁愿冒再度沦为奴隶的危险,留在汤姆身边细心服侍他。但这种服侍,不是对白人奴隶主的卑躬屈膝,而是对朋友、对友谊竭尽忠诚,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助。
马克·吐温的艺术才华是多方面的。《哈克·费恩》的艺术描写表现了马克·吐温独特的艺术风格。最突出的就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所经常提及的“马克·吐温式的幽默”—含有深刻的讽刺和批判的成份,并服从于刻画特殊人物需要的堪称典范的幽默。马克·吐温是一个优秀的幽默、讽刺作家,他不喜好正面抨击,无论是哪个时代自身的问题和弊病,还是不同的文学创作派别。在马克·吐温早期的轻松幽默的作品中,常以“天真汉”,“老实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通过“我”的行事和遭遇来揭示荒谬可笑的社会现象。在小说《哈克·费恩》中,马克·吐温借哈克之口,直观具体地叙述孩子的真实感受,自己并没有站出来宣讲主题、表明倾向。这样,不同读者对作品的倾向有了不同的理解,对小说中暗示、象征作了五彩缤纷的阐释。因此,马克·吐温在不同章节叙述上面所提事件的主旨只有一个:表明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在美国达到顶峰时期。南北战争后,乡土文学迅速崛起,以殖民文化为特征的浪漫主义文学走向衰落。然而,东部的雅士们却无视现实生活的变化,在文学上仍然筑壕自守、抱残守缺,热衷创作一些无病呻吟、悲悲凄凄的感伤诗。与此同时,反映西部边疆人们真实生活的乡土文学也逐渐成熟。这样,东部的“雅”与西部的“俗”产生冲突,不能雅俗共赏。马克·吐温代表乡土文学派,以广阔沸腾的西部为鼓吹阵地,用方言口语体现本土人民真实而平凡的生活,为土生土长的美国文学诞生奔走呼号,摇旗呐喊。
随着社会变化,时代变迁,人们的审美需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战前那种醉心于梦想、幻想的浪漫主义情调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那种自哀自怜,声声叹息死亡的诗,以及神奇、瑰丽的司各特式小说,也反映不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愿望。事实上,人们希望有一种文学把人和人的生活描述得如同自己经历过、看到过、感受过的那种逼真,从而能在小说中照见自己和周围人的影子。而马克·吐温正是从实话实说的角度,从关注人和现实命运方面,描述人真实而平凡的存在,讲述百姓平谈的生活。在《哈克·费恩》里,马克·吐温借哈克和汤姆之口,给那些迷恋于传奇浪漫的贵族雅士们当头一棒,迎头痛击,让他们伴随着轮船沉到海底,或者象小诗人“哀梦兰”那样短暂。
作为十九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小说《哈克·费恩》体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马克·吐温别出心裁的创造表现在他善于将纷然杂呈的现实生活场面组织成盎然有趣的故事,并善于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现象和自然风光的描述中寄寓深刻的思想。
古往今来,儿童传奇小说和历险小说可谓汗牛充栋,但象《哈克·费恩》一样展示如此丰富的生活画卷,包含如此深刻的思想作品却是凤毛麟角。小说通过顺流飘荡的一叶木筏体现了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图景:凋蔽的农村、贫富的对立、凶恶的世仇、残酷的种族压迫……,形象地反映了南北战争前后的美国社会。小说的出版,震动全国。人们被这一野蛮、残酷的族仇吓得“毛骨悚然”。 因为这不是向壁虚构的故事,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对南北战争以后喧嚣一时的“美国民主”无乃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小说中这种对现实生活的精雕细刻与密西西比河的风光的抒情描写以及引人入胜的历险故事揉合在一起。天然浑成,美不胜收的密西西比河风光与虚伪狰狞的资本主义“文明”互为对照,丰富多彩的冒险经历与枯燥乏味的学校生活相比较。这种烘托对照的手法不仅给人以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的教育,而且使得小说错落有致,摇曳多姿,并从而把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紧紧结合在一起。
轻松的幽默与犀利的讽刺熔于一炉,这是马克·吐温创作的一大风格,也是这部小说的显着特色。小说《哈克·费恩》通篇语言浅白简精,一目了然,不事雕琢,遣词造句符合哈克和吉姆的身份。这种“以自然之舌言情”的风格使作品蕴含若隐若现,引人遐想。马克·吐温在作品中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文学观,而是有意隐去自己的看法,留下一片空地,让读者自己去咀嚼、品味、想象。他主要运用象征与反讽艺术技巧,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寓庄于谐,含沙射影的幽默使得小说读起来妙趣横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从这些象征实体结局看,马克·吐温对“雅文人”的文风嗤之以鼻,对他们缅怀昔日殖民文化的“雅”,沉醉于个人情感的“雅”,不关心普通人民疾苦的“雅”深恶痛绝。但是,这些象征实体与象征意义的象征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们不荒谬,不难以想象,这些意象都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模式,洋溢着写实主义品格的象征。这使得《哈克·费恩》百来以来一直吸引众多人的兴趣,成为老少皆宜的小说。
马克·吐温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战士和倾向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他却从不正襟危坐,板脸说教。他善于将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现象集中、提炼、加工成含义深刻的笑料,使读者在赏心悦目、前俯后仰之间受到熏染、教育和启发,憎其所憎,爱其所喜:骗子“皇帝”和“公爵”的狼狈下场,令人抚掌;吉木的迷信和吹牛不失为忠厚善良;汤姆、哈克的淘气捣蛋正显示了他们的聪明可爱……。作者不直接褒贬自己笔下的人物,但通过人物举止言谈的绘声绘色的描写,作者的好恶之情却跃然纸上。
马克·吐温是“讲笑话的高手”,但“讲笑话”决不是他的目的,而仅仅是一种手段,他把萨克雷的一段名言奉为创作金箴:幽默作家承认自己的目的在于唤起和指引你的爱,你的同情、你的仁慈,即你对虚伪、傲慢、蒙骗的蔑视以及你对孱弱、贫困和不幸的侧隐之心……“他评论生活中常见的行为和激情。” 他把“笑”视为一件真正的武器,“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得住笑的攻击。”马克·吐温的这种将幽默与讽刺溶于一炉的崭新风格取代了当时流行的插科打浑,浅薄无聊的幽默文风,为美国文学的巨大发展做出了贡献。
除运用象征技巧之外,马克·吐温还运用反讽技巧中的反话正说和滑稽摹仿,嘲笑和挖苦哀怨的感伤诗以及魔幻般的传奇小说。
马克·吐温假借哈克纯真之口,感叹诗人“哀梦兰”后继无人:“这位薄命的哀梦兰生前给所有的死人作诗,以示哀悼,到如今她人死魂飞,竟没有人给她写一着挽歌。”哈克一面赞美少女“哀梦兰”诗写得好,甚至想摹仿创作一首献给她,以示哀悼;一面又说“我自己绞尽脑汁,想写一两首,可是不知为什么缘故,总是写不出来。”这些自相矛盾的话语既有一份孩子天真,又有一份深奥,读起来令人发笑、发人深思。这里,马克·吐温婉转含蓄地表明了自己追求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的现实主义创作标准。
小说在语言上的运用也是别开生面的。这表现在:首先是方言口语的妙用。为了刻划人物性格,为了加强语言表达力,马克·吐温大量熔合、提炼、吸收方言、口语,小说中运用了密苏里的黑人土话、西南边疆的地区方言、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普通方言及其四个变种。言为心声,语随人异,方言土语的妙用加强了小说的生活气息,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其次是创造了一个简洁的文体。马克·吐温深悉语言的简洁之道。为了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马克·吐温往往不惜浓墨重彩,竭尽夸张,对人物的外形和服饰则是惜墨如金。小说对人物的穿着衣戴、高矮胖瘦,几乎未作交代,可是他们的形象却深深地印进了读者的脑中,画龙点睛,以少胜多,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这正是马克·吐温的高明之处。
马克·吐温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如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准则。他曾经说过,“我最终的理想和愿望是能做到‘真实’,能说自己‘真实’”。
《哈克·费恩》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作品,象大自然中自由生长的野花一般生命力旺盛。哈克的方言和吉姆的土语使该小说不再是雅致的摆设,而是构划密西西比河畔浓郁的风土人情的工具。马克·吐温的叙述就象滚滚前进的密西西比河一样,滔滔不绝,它自然连贯,把整个故事组织得天衣无缝。正象海明威所赞赏的那样:“这是一部最好的书。所有的美国文学都源自此书。以前没有一本书能与它抗衡,现在还是一样。”